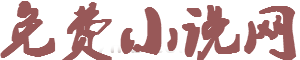第1931章
作品:《从噩梦到天堂离婚四年的成长史连载》四、亡命天涯
在文革前的几年里,虽然农村还实行人民公社制度,但由于实行“三自一包”,几年之中农村还是出现了微小的贫富分化。勤俭持家的人稍微富裕一些,好吃懒做的人要相对穷一些。前面提到的郑八虽然是村治保主任,但好吃懒做、挥霍无度。那时他们家吃饺子饺子馅里竟然不搀青菜,纯粹是精肉馅的。这种过日子法,在当时一般农民中都是不敢想象的。因此,郑八家里始终是家徒四壁。郑八的几个孩子从生下来一直到文革,居然没有盖过被子。文革一开始,郑八就带着他的几个儿子来我们家抄家,把被子都抱走了。几个儿子晚上把抢来的被子往身上一盖,兴奋地说,原来盖被子睡觉竟然这么舒服。其实当时的中国,除了少数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以外多数人都是赤贫的,也非常可怜。但高明的统治者恩赐给这些可怜的人一个乐趣:从人群中划出“极少数”更可怜的一群来让这些人折磨、虐待,从受虐者的惨状中让那些折磨他们的人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感觉。
随着造反派日复一日的折磨,外婆的身体越来越差,腹部肿得像一口大锅。外公比较麻木,不会多想,身体也比较硬朗,倒是还扛得住;而外婆这个人自尊心强,忍受不了这种侮辱,就跑到村外上吊自杀,幸亏被人发现后救下来了。此事发生以后,造反派们就当着外婆的面对我外公和母亲宣布了一条纪律:每天必须看着外婆,不许她自杀;如果外婆自杀了,那么就拿外公和母亲是问。外婆怕牵连外公和母亲,只好放弃了自杀的念头。这就是那个时代:求生不能,求死也不能。
外婆自杀未遂并没有激起这些平时互相以“自家”、“亲自家”相称的造反派们的丝毫怜悯,依旧不依不饶。而且,随着“斗争经验”的日益丰富,批斗的手段也越来越毒辣:在游街时,把这些戴着木牌高帽的批斗对象用绳子拴成一堆,弄一些威力大、声音响的二踢脚往他们头上扔。伴随着“嘭嘭”的巨响,一边是这些老弱妇孺们惊恐万状地躲避,一边是兴致勃勃的造反派们开怀大笑。每到此时,外公和外婆都紧紧地护住我母亲,生怕她年纪太小禁不住吓出个三长两短。有个精神脆弱的批斗对象,从此吓疯了。
其实,外公、外婆和母亲所受到的这些迫害,在当时来说还并不算特别恐怖的。文化大革命期间,有很多地方发生了针对成分高者的屠杀行为,有的全家惨遭灭门之灾。例如湖南省道县,在一九六七年夏季短短两个月之内,就有四千多名家庭出身不好的人被残杀,上至八九十岁的老人,下至几个月的婴儿,都不能幸免;其手段之残忍,方法之暴虐,令人发指。比起他们的命运来,外公、外婆和母亲的遭遇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
恐怖的利斧不仅仅砸落到我们家头上。当时大队长的女儿小名叫改改,就是那个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、经常欺负我母亲的女孩。改改在文革初期也成了红卫兵,最初抄家、批斗别人的时候也是耀武扬威。只过了几个月,他爹因为粮食关时贪污引起众怒被整倒了,改改也霎时间从神气活现的批斗者、红五类成了批斗对象、黑七类,惊恐不安地和我们家一起受刑。改改他爹脾气大,挨批斗没几天就气死了;改改他妈受不了这种刺激,不久就疯了。我小时候在农村住时,还经常见到这个疯老太太深更半夜要去公社“告状”。改改也慌忙在离家五六十里地开外的一个村子找了个婆家嫁了。改改的模样和人品都不怎么样,又是黑七类,正经人家不要,只好找了一个瘸子。
在一九六七年春末夏初的一次批斗中,一枚威力巨大的二踢脚在我母亲耳边轰然炸响,把十五岁的她的右耳炸聋了。那次批斗结束后,外婆对我母亲说:“秀菊(【注】我母亲的小名),这老家实在是没法活了,我和你叔(【注】滑县方言管父亲叫“叔”,母亲叫“婶”)也算是活够了,不怕死……可你还小,赶快找个好人家逃命吧!再待在家里也不知道哪一天就没命了!”当时,聋着一只耳朵的母亲已经被吓得神情恍惚,茫然地点点头答应了。
然而奇怪的是,尽管我们家是“贱民”,但当外婆放出话来给母亲寻婆家时,前来说媒的人却络绎不绝。很多提亲的对象,不是这个村的支书,就是那个村的民兵队长。其中原由就是我母亲模样长得非常漂亮,又被外婆教育得极为贤惠。尽管批斗我母亲时这些人可以高呼口号,甚至动手打人,但他们心里并非不清楚是非。陷害别人是为了保全自己,或者是捞取向上爬的政治资本;而现在利益就在眼前,什么阶级立场、阶级感情都立刻不重要了。这就是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“触及灵魂的大革命”洗礼后,中国人整体所具有的心态。
但是我的外婆对滑县这块土地早已恐惧万分,宁死也要把母亲送得远远的,因此对支书儿子、民兵队长们的求婚,一概婉言谢绝。就这样,我在郑州的大姨找了住在郑州拾破烂的老乡张大娘,由她把我母亲介绍给了我父亲。那是一九六七年九月,我母亲十六岁,我父亲三十二岁。
本章已完成! 从噩梦到天堂离婚四年的成长史连载 最新章节第1931章,网址:https://www.254y.com/53/53836/1932.html